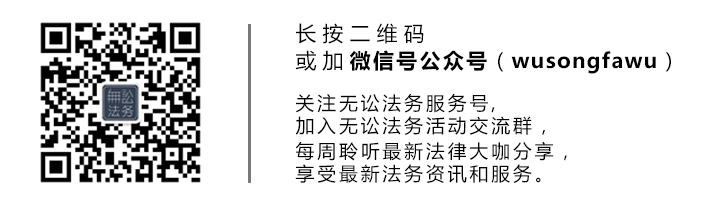编者案
近日来发生的运钞车枪击案还没热起来就冷下去了,或许是由于大家觉得砸车者咎由自取死有余辜,抑或者因为本案开枪者乃公务人员而无“心同此理”、感受不深。尽管如此,本期编者说的作者以为本案仍有讨论的价值,以图对案件的事实与法理进一步认识。
文/张召怀 《清华法律评论》编辑
本文由“清华法律评论”授权无讼阅读发布,转载请联系清华法律评论
一、基本案情
在此根据网上公开的资料,并在去除相关倾向性、情绪性用语的基础上,归纳出大致案情如下:
当天中午12点,运钞车在经过十字路口时与等待红绿灯的男子黄某发生碰撞,致使黄某倒地。但运钞车并未停车了解情况而径直前行。可能黄某因此而被激怒(其家人事后表示黄某性格倔、认死理),开始追赶运钞车。运钞车暂时停在了下一路口,黄某追上后从路边捡起砖头打砸运钞车的窗玻璃。(此时押运员如何反应不知)不久运钞车继续往前行驶,在下一路口停车时再次被黄某追上,黄某继续打砸窗玻璃,致使窗玻璃破损严重,一名运钞员开窗大声警告黄某,要求其停止打砸行为,另一名运钞员则立即报警。但黄某对警告不予理睬,继续打砸。于是运钞员开枪(防暴枪、橡胶子弹)、黄某倒地、抢救无效死亡。事后据称,开枪的押运人员梁某已经被立案调查。
二、开枪者的刑事责任
(一)正当化事由的判断
梁某故意开枪致使黄某死亡,其行为客观上符合了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如果不存在违法阻却事由,也不缺乏相关责任要素,则梁某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本案的核心则在于分析是否存在违法阻却事由。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违法阻却事由包括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这两种类型,从违法的实质来看,理论还承认法令行为(职务行为)、正当业务行为、被害人承诺与义务冲突等违法阻却事由。从网上报道来看,基本上都在考虑防卫与过当的问题。本文认为本案中不适用正当防卫,应该考虑职务行为这一违法阻却事由。
1.对正当防卫的否定
网上许多报道都是从防卫的角度来考虑梁某的开枪行为,认为黄某拿砖头砸车的行为是一个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梁某的行为则是为了制止该不法侵害以保障押运财物及自身的安全,属于正当防卫的范畴,只是需要考虑这里是否存在防卫过当的问题。
本文认为,这一分析进路存有疑问。首先,从正当防卫的性质来看,通常认为正当防卫属于公民的防卫权,是一项权利,因此在面临不法侵害时,公民可以选择积极地正当防卫,也可以选择消极地回避侵害。但在本案中,运钞员负有保护车载财物的义务,在面临针对财物的不法侵害时,运钞员只能选择直面危险,勇敢地保护财物免遭侵害,而不可以简单地丢车逃离,这就决定了对运钞员不可适用刑法中的正当防卫条款。其次,刑法第二十一条第三款规定,“第一款中(注:紧急避险)关于避免本人危险的规定,不适用于职务上、业务上负有特定责任的人。”如所周知,紧急避险的适用受到严格限制,避险权限也极小,而正当防卫的权限相对较宽。举轻以明重,在职务上、业务上负有特定责任的人连紧急避险都不被允许,更何况是权限更大的正当防卫呢?再次,正当防卫不受比例原则的严格限制,既不要求保护较大的利益,也不要求手段的必要性和程序性,特定情况下还允许进行无限度的防卫;与之相反,职务行为需要严格符合比例原则,既要求保护较大的法益,同时还要求采取的必须是必要的最小限度手段。此外,在开枪的场合,还有严格遵守法定的程序,通常情况下应当先口头警告,然后鸣枪示警,最后才能开枪,而且应当在制服可能的情况下先朝非要害部位开枪。(当然在特定情况下也可以在警告后径直开枪,而不需要鸣枪示警,比如枪里只有一颗子弹时。)最后,特定情况下负有职责的人在制服不法侵害人后还需要抢救不法侵害人,因为这也属于其职责范畴,但正当防卫则无此要求。还需要提及的是,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曾在1983年联合发布了《关于人民警察执行职务中实行正当防卫的具体规定》,在该规定中允许人民警察“正当防卫”,但在2004年公安部在《公安部关于保留修改废止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通知》中废止了前述规定,允许人民警察正当防卫的最后一根稻草也被拔掉了。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认为,在判断梁某开枪的正当性时,由于梁某属于负有特定职责的人,此时不可根据正当防卫的条件来判断其行为,相反,应当以更为严格地职务行为来分析。事实上,尽管各报道在用正当防卫来分析梁某的行为,但同时也都根据《专职守护押运人员枪支使用管理条例》等来分析梁某的行为,因此虽然冠之以正当防卫的名,但实质上还是利用了职务行为之实。
2.对职务行为的肯定
如前所述,本文认为应该根据职务行为来判断梁某的行为,此时需要通过相关法律法规来考察梁某的职责,进而判断其行为正当与否。
《专职守护押运人员枪支使用管理条例》:
第五条专职守护、押运人员执行守护、押运任务时,能够以其他手段保护守护目标、押运物品安全的,不得使用枪支;确有必要使用枪支的,应当以保护守护目标、押运物品不被侵害为目的,并尽量避免或者减少人员伤亡、财产损失。
第六条专职守护、押运人员执行守护、押运任务时,遇有下列紧急情形之一,不使用枪支不足以制止暴力犯罪行为的,可以使用枪支:
(一)守护目标、押运物品受到暴力袭击或者有受到暴力袭击的紧迫危险的;
(二)专职守护、押运人员受到暴力袭击危及生命安全或者所携带的枪支弹药受到抢夺、抢劫的。
第五条确立了使用枪支的基本要求:最后手段、最小伤害。紧接着第六条从正面明确规定了开枪的情形:守护目标受到暴力袭击或押运人员受到生命威胁(被抢夺枪支的情形也可谓生命受到威胁)。因此,根据这两条,可以认为:只有在暴力袭击(守护目标或者人身),其他手段无效时,才可以使用枪支,并且只能造成必要的最小伤害。
中国人民银行、公安部关于印发《关于银行守库、押运人员在执行任务中使用武器的规定》的通知:
一、银行(包括人民银行和各专业银行)的守库、押运人员负有特定任务。在执行守库、押运现金、金银、有价证券任务中,为保卫国家财产安全,遇有下列情形之一时,可以使用武器:
(一)守库、押运人员的保卫目标受到暴力侵袭或者有受到暴力侵袭的紧迫危险,非开枪不能制止时;
(二)守库、押运人员佩带的武器,遭到暴力抢夺,非开枪不能制止时;
(三)押运人员护送现金、金银等财物的交通工具(包括机动车辆和非机动车辆)遭到暴力劫持,非开枪不能制止时;
(四)守库、押运人员和运送现金、金银等财物的车辆驾驶人员人身遭到暴力侵袭,非开枪不能自卫时。
二、守库、押运人员在上述四种情况下,对不法侵害人开枪射击只限于使其失去侵害能力;除特别紧迫的情况外,应先口头或鸣枪警告,如果不法侵害人有被慑服的表示,或者已经丧失侵害能力,应即停止射击;事后要保护现场,并立即向本行领导和当地公安机关报告。守库、押运人员为保卫国家财物使用武器进行防卫时,必须注意避免伤害其他无关人员。
第一条确立了使用枪支的四种情况:守卫目标受到暴力袭击、武器受到暴力抢夺、交通工具受到劫持、人身受到暴力袭击。第二条则确立了开枪的限制条件:使其失去侵害能力为必要、(除紧迫情况)口头警告和鸣枪示警、制服后及时停止、保护现场。
综上所述,押运员开枪行为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只有在特定场合才能采取特轻的开枪手段。具体到本案:首先,守卫目标是否受到暴力袭击?黄某用砖头打砸的对象为押运车,此时即便可认为押运财物造成了威胁,但此时仍然可通过其他手段来保护押运财物,比如将车驶离现场,毕竟是车与板砖作战,车还是占据明显优势的,因此开枪并非最后手段。其次,这里也不存在武器受到暴力抢夺。再次,交通工具是否受到劫持?这一条可能和案件联系最为紧密,但是黄某仅为打砸押运车,虽然玻璃严重受损,但说“劫持”则远远谈不上。最后,押运人员生命是否受到威胁?本文也持否定看法,押运人员身处于装备特殊的押运车辆内(黄某多次打砸也仅造成玻璃破损),黄某采取的手段——板砖——杀伤性较小,即便押运人员直面黄某,由于押运员都是受过特殊训练,在肉搏上也占据优势,因此难言生命受到威胁。根据这些理由,本文认为,梁某开枪致黄某死亡的行为,不属于正当的职务行为,其行为已经过当,无法阻却其违法性。
(二)对责任的分析
1.类“假想防卫”的否认
或许可能认为,由于押运员梁某当时误认为存在一个紧迫的暴力袭击,比如有人来劫持押运车,抢劫押运财物,由此才开枪,这样就类似于“假想防卫”,存在一个“假想的正当职务行为”,如果这样的话,就可以否定故意的责任。但是,梁某是否存在这种误想,值得怀疑,一方面当时是在光天化日、人员众多的十字路口附近,不远处还有交警大队,在这种环境下发生此类胆大妄为的事情的可能性小,另一方面黄某仅只身一人,且采取的手段为板砖,难以让人认为其在抢劫。即便梁某存在这种误想,也要求梁某的行为在如其想象的情况下符合正当职务行为的要求。如前所述,尽管在(假设的)梁某想象的情形中,梁某可以开枪,但开枪行为仍然有严格限制:口头或鸣枪警告→只限于使黄某失去侵害能力。梁某的行为也明显不符合该要求,故而也不属于“假想的正当职务行为”。
2.对“误认职务行为的权限”否认
或许还可能认为,这里梁某误认了其职务权限,以为在碰到有人严重打砸押运车时,只需要口头警告无效后就可以当场击毙。这属于对职务权限的误认,又被称为“允许的错误”,属于违法性认识可能性的范畴。如果该错误不可避免,则阻却其责任;如果存在该错误但具有避免可能性,则可能减轻其责任。但本文也否认这种情形的成立,根据《专职守护押运人员枪支使用管理条例》第三条,押运人员必须“经过专业培训,熟悉有关枪支使用、管理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并且需要“由所在单位审查后,报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审查、考核”;《中国人民银行枪支管理规定》第十条和第十四条也做出了相类似的规定。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难以认为梁某对枪支使用规范缺乏认识,存在错误。
(三)对量刑责任的分析
根据刑法第二十条第二款,“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刑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紧急避险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在本案中,梁某的行为属于过当的职务行为。尽管刑法没有规定过当的职务行为的处罚原则,但是否可以类推适用前述两款规定,也对梁某“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诚然,将我国刑法关于防卫(或避险)过当的减免处罚规定类推适用于过当的职务行为,并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因为罪刑法定原则所禁止的只是不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而不禁止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任何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都具有妥当性。本文认为,对于过当的职务行为,不能类推适用防卫过当、避险过当的处罚规定。在分析这个问题时,首先应当明确防卫过当和避险过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正当化根据是什么,然后考察过当的职务行为是否也存在该正当化根据,最后判断是否可以类推适用其规定。
通常认为,之所以对防卫过当和避险过当“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是由于违法的减少和责任的减少。由于防卫(或避险)行为保护了特定的法益,因此在不法衡量中减少了行为的违法性;由于防卫(或避险)行为属于紧急情况下的举措,在紧急情况下一般人由于内心恐惧、害怕、慌乱(又被称为“虚弱效应”)等特殊心理而难以控制行为的幅度,此时难以期待一般人实施适法的行为,因此期待可能性减少。但在职务行为的场合(以本案为例),一方面,梁某不仅负有保护财物的行为,而且也有防止造成他人不必要的损害的义务,因此违法性减少的幅度很小;另一方面,梁某是受过特殊训练的人,他在面对黄某的违法犯罪行为时,一般不会也不应当产生恐惧、惊慌心理,因此其过当的职务行为并不使其责任减少。
综上,对梁某过当的职务行为不应当类推适用防卫(或避险)过当的减免处罚的规定。
三、被害人的“作”与责任
在知乎上“如何评价东莞男子用砖头砸运钞车,被防暴枪(橡胶子弹)击中后经抢救无效死亡?”一文中,获得高票支持的署名为“高天”的答主提出了“灰色地带”说法:“实际上,哪儿有什么线。你觉得对,他觉得他对罢了。真正的线,有两条,一条在远方的灰白交界,一条在远方的灰黑交界。要想干干净净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你唯一的选择是远离灰色地带。”或者这句话还有点儿模糊,通过这句就清楚了:“为什么我们要去在一个灰色地带分出黑白?这件事的最终意义,真的是谁对谁错么?”根据本文的理解,答者应该是指,这里不是梁某对、黄某错或者相反,争论这类对错没有意义,黄某一开始就不应该往枪口上撞。正如下面评论中有人指出,“能把‘傻逼敢不敢不犯贱,命是自己的’说的这么委婉又不失重点,牛逼!”
本文不赞同上述观点,上述观点更像是事后父母教导孩子远离危险场所,做一个安静地好孩子,以避免遭受灾祸,不然就是自作自受。说得更为极端点,这其实是一种良民心理和弱者心态,在遭受侵害时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做错了什么,之后应该如何避免。在被抢劫时,认为自己不该走行人稀落的小路;在被强奸时,认为自己不该穿着过于暴露。但正如曾有人言,“我可以骚,但你不能扰。”被害人的“过错”并不代表自作自受,即便是“作”,也仅应当承受与之相应的责任。被害人有过错,并不因此就否定了侵害人的过错。
本案所涉并非对错有无,而是对错大小的问题,并非我们否定了梁某行为的正当性,就肯定了黄某行为,反之亦然。问题的关键在于,尽管黄某作,他的行为是否就活该挨这一枪子。常言道,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倘若以眼还牙,就并非自作自受,这就违背了我们基本的正义观念。
前段时间发生的延庆动物园老虎伤人案,许多人也认为该女子违反规定下车是“咎由自取”。与此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为保护一名企图自杀的男子,智利圣地亚哥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便被迫击毙了两头狮子;美国辛辛那提动物园为救一名“从天而降”的3岁儿童,也枪杀了一头知名的银背大猩猩。在这些案件中,虽然都是被害人“作”,但国外的做法表明,被害人并不因“作”而就该被“判死刑”。
编排/卢明亮
责编/张洁 微信号:zhengbeiqing07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