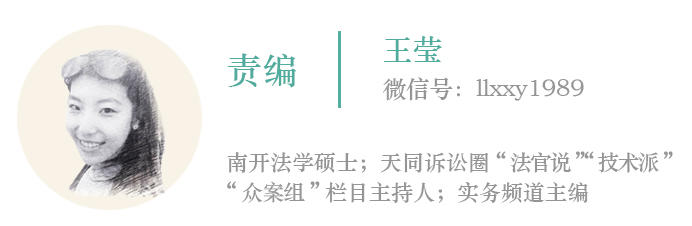文/何家弘
来源/何家弘的法律博客
孟勤国教授是《法学家茶座》的老作者,我喜欢他的文字,因为既有思想性,也有可读性。但是,由于研究专业的差异,我以前没有读过他的学术论文。这次他在《法学评论》上发表的论文引起了争议,也为我提供了拜读的机会。我以为,学者就自己熟悉的个案来剖析司法裁判的缺欠及背后的法学理论问题,本是无可厚非的。如果其他学者不认同文章中的观点,也应该以学术争鸣的方式进行论争。孟教授这篇文章中涉及的民事法律问题,我不熟悉,不能评判,但是从证据法学的角度来看,这篇文章确实存在小小瑕疵,主要涉及“自由心证”的概念。
什么是“自由心证”?人类社会的司法证明制度有两种基本模式。其一是“规范证明”(或译为“法定证明”),即法律为司法证明活动设计了具体的规则,司法者在采纳证据和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时候必须遵守这些规则,譬如法国16世纪的“法定证据制度”。其二是“自由证明”,即法律对司法证明活动没有任何限制,司法者在诉讼过程中可以自由地采纳证据并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譬如法国19世纪初确立的“自由心证制度”。
1808年法国《刑事诉讼法典》对自由心证制度做出了具体而且生动的规定。它以陪审团审判为例,要求法官在陪审团评议案情之前做出如下告知:法律并不要求陪审团讲出他们获得确信的途径方法;法律也不给他们预定的规则,要求他们必须按照这些规则决定证据是否完全和充分;法律所规定的是要求他们集中精神,在自己良心的深处探求对于控方提出的针对被告人的证据和被告人的辩护证据在自己的头脑中形成了什么印象。法律并不对他们说:“你们应当把多少证人所证明的每一个事实认定为真实的。”法律也不对他们说:“你们不要把那些未经某种口头证言、某种文件、某些证人或其他证据支持的证据视为充分的证明。”法律只是向他们提出一个能够包括他们全部义务的问题:“你们是内心确信了吗?”因此,以法国为代表的自由心证制度又称为“内心确信”的证据制度,其基本内涵就是要通过自由证明达到内心确信的程度。
自由证明模式和规范证明模式是各有利弊的,因此当前世界各国的司法证明制度多属于两种模式的中和,但有所侧重。而且,许多国家都是在采纳证据的问题上取规范证明,即由法律规定了证据采纳规则或证据排除规则,而在采信证据的问题上取自由证明,即让司法者依据内心良知和生活经验去评断证据的真实性和可信度。由此可见,司法证明只在没有法律规则的地方采用自由心证。诚然,自由心证并不是法官的随心所欲和恣意裁断,但是采取自由心证的前提是没有法律规则,或者说,人类还没有能力制定出这样的法律规则。如果有了法律规则,那就要遵守规则,那就不是自由心证了。这篇文章的标题是“法官自由心证必须受成文法规则的约束”。必须受成文法规则的约束,那还是“自由心证”吗?这个标题本身似乎就不太严谨。
窃以为,孟教授大概混淆了“自由心证”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在司法裁判活动中,自由心证属于事实认定的范畴,不属于法律适用的范畴。由于法律规则——无论是实体法规则还是程序法规则抑或证据法规则——多具有一定的抽象性甚至模糊性,所以法官在适用法律规则的时候往往要行使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但是,这种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并不等于自由心证。我注意到,一些司法人员有时也把法官适用法律规则时的自由裁量说成“自由心证”,但那是误说。学术论文使用概念应该严谨,更不可以讹传讹。再者,这篇文章中批评法官的裁判失当恐怕也很难都归结为自由心证的问题。例如,举证责任的分配不当是法律规则的适用问题,就不属于自由心证问题。顺便说,文中关于“证据是案件事实的要素”以及“证据相关性规则”的论述也值得商榷。
我写这篇小文的目的是希望学术批评能够回归学术。当然,我的观点也可能是谬误。
实习编辑/陈若曦
为无讼供稿/tougao@wusongtech.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