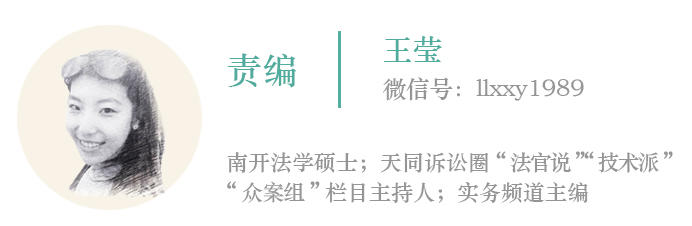文/易延友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新浪博客
引言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民商法博士生导师孟勤国教授在武汉大学主办的《法学评论》2015年第2期以“法官自由心证必须受成文法规则的约束”为题发表论文(以下简称“孟文”),对最高法院(2013)民申字第820号民事裁定书(以下简称“最高法院裁定书”)进行解剖,从关联性、举证责任、证据的证明力以及常情常理等角度,对最高法院判决进行了批判,并指出法官自由心证必须受成文法规则的约束。该文在微信圈十分火热,也引发了大学教授作为曾经的案件代理人是否可以就法院判决撰文评判的讨论。我对民商事法律规则并不精通,但是孟文除第一部分介绍案情概要和裁判要旨和第五部分充满火药味的评论以外,其余部分主要都是从证据法而不是民商法的角度进行论述。对于证据法学,我还是略知一二的。但是看完孟文之后,发现孟文提出的很多论断我实在难以苟同,加上孟教授自己在回应中也呼吁大家关注他论文中探讨的实质性问题,因此也就大胆地撰文,就有关证据法的问题向孟教授请教。
特别声明:我一不认识孟教授,二不认识本案三级法院裁判中的任何法官,三不认识本案双方当事人,也与这些人从未有过接触,跟所有这些人都没有任何过节,也没有任何恩怨,只是从证据法的专业角度,谈谈对孟文所涉之证据法问题的看法。
一、案情简介及主要争点
本案被告新和成公司前身为某县两所中学于1989年共同出资成立的化工厂,原告商志才于1992年4月被某县教育局借到该厂工作,被聘为总工程师。1994年,该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革,经职代会表决并经体改办批复同意,将207.9万元企业集体股权折合为20790股,作为优待股量化到干部职工;商志才获得620股优待股;同时,该公司又面向社会发行现金股,商志才以自有资金1.65万元和向该工厂借贷所得的18万元购买了1965股现金股,合计持股2585股。在此期间,商志才一直和其他职工一样领取工资和奖金。
1995年7月,商志才与化工厂的借用协议终止,到浙江大学读博。1996年和1997年,该化工厂均按2585股给商志才分别发放了1995年和1996年的股份红利。1998年,商志才决定留校(浙江大学)任教,该化工厂决定终止商志才持有的620股优先股,按1375股发放了1997年度的红利;同时按2.3倍溢价由职工持股会回购了商志才持有的1375股现金股。至于剩下的590股现金股,按本案被告的说法及法院的认定,是由于原告商志才未能按期偿还应缴还的红利,已由化工厂根据《借款协议》抵债。
对于上述事实,双方没有争议的事项是:(1)商志才一共持有化工厂2585股,其中优待股620股,现金股1965股;现金股中的1375股已经由化工厂购回;(2)现金股中的一部分系商志才从化工厂贷款购得,双方签订由《借款协议》;(3)商志才于1992年4月借用到化工厂,到1995年7月终止借用协议,1998年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不再回原化工厂担任总工程师职务。双方存在重大争议的事实是:(1)规范层面,商志才认为化工厂无权终止商志才持有的620股优先股;事实层面,商志才持有的化工厂620股优待股并未终止;新和成公司则认为,化工厂有权终止,事实上已经终止;(2)新和成认为化工厂有权扣除商志才持有的590股现金股冲抵应缴红利,事实上已经扣除且商志才并无异议;商志才则认为化工厂无权扣除,且从未认可化工厂扣除其590股股权冲抵债权的事实。
二、关联性的定义及其含义
所谓关联性,就是指“一个证据对于能够决定案件结果事实之存在与否比起在没有这项证据的时候更有可能或者更无可能的趋势”。这是美国《联邦证据规则》对证据关联性下的定义。我国法律均没有对关联性作出明确的界定。不过,孟勤国教授显然并不反对这个定义,因为孟教授认为“证据相关性规则无论是在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在大陆法系国家都是证据规则之王”,可见孟教授至少是认可英美法系的关联性规则的,那么作为英美法系证据立法的最高典范美国《联邦证据规则》有关关联性的界定,我猜想孟教授一定是认可的。
根据这个定义,任何一项证据要满足关联性的要求,都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实质性,也就是该证据所指向的证明对象必须是能够决定案件结果的事实;如果证据指向的待证事实对于能够决定案件结果的事实毫无作用,则该证据因不满足实质性要求而不具有关联性。例如,某男教授(甲)起诉某女律师(乙)欠款160万,甲起诉乙的事实是乙欠钱不还。在这一简单的债务诉讼中,乙是否欠钱不还就是能够决定案件结果的事实。假定乙承认确实与甲有金钱往来,不过不是借贷,而是赠与,并举出视频证据证明甲曾经向乙说过暧昧的话,以此证明甲与乙并非简单的师生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视频证据具有关联性。但如果乙承认借过钱,但主张钱已还,也举出前述视频证据,这个证据因与决定案件结果的事实没有关系,就不具有关联性。可见一个证据是否有实质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所指向的证明对象,以及这个证明对象和能够决定案件结果的事实之间的关系。
二是证明性。证据必须对于待证事实的存在或者不存在能够产生一种“比起没有该证据的情况下更有可能或更无可能的趋势”,这就是证明性,其实就是对证明力提出的要求。仍然以甲起诉乙欠债不还为例,假设甲在法庭上出示了一个鸡蛋,说我用这个鸡蛋证明乙欠债不还,但却不说明这个鸡蛋和乙欠债不还之间有什么关联。我相信所有具备正常理性的人都不会同意甲的看法,因为这个鸡蛋对于乙欠债不还这一事实究竟是否存在对法官内心确信的形成没有任何影响。法官除了觉得奇怪以外,既不会因为这个鸡蛋相信乙欠债不还多一些,也不会因为这个鸡蛋相信乙欠债不还少一些。因此这个鸡蛋由于缺乏证明性而不具有关联性。
值得指出的是,关联性虽然被认为是证据的基本属性,但是它并不是内部属性,而是外部属性。因为,任何证据与案件结果事实之间的证明性都是需要人类凭借经验与理性进行逻辑推理的。的确,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客观事物之间的联系都属于内在联系。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地中海的蝴蝶煽动翅膀,和太平洋西岸的台风也有联系。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这种内在联系是一种哲学上的概念,并非证据法上的概念。如果照搬哲学上的概念,证据法上的关联性就可以取消了,因为按照哲学上的观点,所有客观事物都是普遍联系的,孤立的不与任何事物发生联系的事物是不存在的。那还要将关联性作为证据的可采性条件做什么呢?因此,尽管从哲学上讲地中海的蝴蝶煽动翅膀也许和太平洋西岸的台风有关系,在证据法上这种关联性却不是不证自明的,而且,要证明这两个事实之间的关联性,无论对于生物学家、气象科学家和地球物理科学家而言还是对律师而言,都并非易事。因此,证据法上的关联性只能是外部属性。
例如,在大家都熟知的聂树斌案件中,警方在杀人现场也就是离尸体不远的玉米地里发现了一串钥匙。这串钥匙和聂树斌杀人这一案件核心事实之间有什么内在联系呢?本来是没有联系的,因为在聂树斌的供述中并没有出现过这串钥匙,所以尽管它出现在案发现场,却与聂树斌是否杀人并无关联。但是由于王书军的出现,由于在王书军的供述中出现了这把十分隐蔽的钥匙,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证明王书军比聂树斌更熟悉现场情况,王书军对现场的描述在细节上的精确性甚至超过了聂树斌,因此是王书军杀人的可能性超过了聂树斌,也就是这把钥匙间接地证明了聂树斌不是杀人凶手这一事实,它在聂树斌申诉案中也就具有了关联性。一串钥匙,在十几年前的聂树斌杀人强奸案中没有关联性,但在十几年后的聂树斌杀人强奸申诉案中却有了关联性,其实是同一个案件,指向的是同样的案件事实,前一阵没有关联性,这一阵就有了关联性,怎么还能说关联性是内在联系呢。可见,孟文关于“证据的相关性”是指“证据内容与有待证实的事实之间的逻辑联系”这一论断虽然正确,但其关于“相关性是指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样的论断,却是不正确的。不得不说,孟文通篇都在正确和貌似正确的证据法命题中夹杂一些完全不正确的论断,给我们分析其论文的思路和反驳其观点造成了十分巨大的障碍。
又如,最近大家都关注的某东与某妹领证结婚的消息,让很多潜在的某妹伤透了心。也许是为了让大家宽心,一个网站列出了某东曾经的三个女人,其中第二个是他的下属某庄。其主要证据是,某东于某年某月某日在微博上晒出了自家阳台上番茄的照片,鲜艳明亮,秀色可餐。同一天,某庄的微博也晒出了同样的番茄照片,色彩、角度、叶片、姿势全都是一样的。两张照片放到一起,证明两人同居。几个番茄,与一男一女同居之间有什么内在联系呢?纯粹都是俗人的胡思乱想而已。
三、本案证据中的关联性
在确立了有关证据关联性的一些基本规则和基本观念之后,我们终于可以讨论最高法院民事裁定书中案件的证据关联性问题。孟勤国教授的论文指出:“本案裁判据以认定商某1210股已被终止和抵扣的书面证据只有三个:章程(草案)、借贷协议和1375股分红单。”孟文还承认,“这三份证据的真实性没有争议,绝大部分内容的合法性也没有争议”,但认为“任何不带偏见而且仔细阅读的人都能发现这三个证据与本案裁判认定的案件事实毫无关系”。本文认为,孟文对这三份证据均与本案无关联性的判断都不成立。
首先来看《章程》(草案)。最高法院裁定书认定:“根据新和成公司当时的章程,职工离厂优待股自行终止,二审法院认定1998年商志才毕业留校离开合成化工厂,其持有的620股优待股即已被终止,并无不当。”这说明,无论是最高法院还是二审法院,运用《章程》证明的事项就是620股优待股已经终止这一事项。620股优待股已经终止这一事项是不是能够决定本案结果的具有实质性的待证事实?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所以《章程》这一书面证据满足实质性这一要求。既然满足实质性要求,那是否满足证明性这一要求呢?按照孟勤国教授的说法,《章程》最多只能证明公司有权终止优待股,不能证明公司已经终止优待股。应当承认,有权终止和事实上终止确实是两码事,一个是规范意义上的,一个是事实层面上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有权终止和事实上终止就完全没有联系。有权终止虽然不意味着必然终止,但是在有权终止的情况下事实上终止的可能性是否更大呢。从经验上来看应当是这样。当然,有了有权终止这个事实并不必然意味着事实上终止,就好像有证据证明家藏万瓶茅台也不一定就能证明天天喝茅台这个事实一样。但是比起没有章程这个证据而言,有章程这个证据,公司依章程终止620股优待股的可能性更大。所以章程具有证明性。满足关联性要求。
需要指出的是,很多证据自身是不能说明自身的关联性的,其关联性的有无其实是有待于它与其他证据共同构成完整的链条才能显示出来的。一把在杀人现场发现的杀猪刀,上面沾满了血迹。如果没有目击证人的证言,没有杀猪刀手柄上的指纹鉴定或者对血迹的血型测定,杀猪刀就是杀猪刀,它和杀人案件也许没有任何联系。但是杀猪刀上也许有被告人的指纹;也许沾满的是被害人的鲜血;也许有目击证人看到被告人用这把刀杀害了被害人。有了这些,杀猪刀与案件就有了关联性。你不能说杀猪刀本身什么也证明不了,所以它就没有关联性。应当承认,《章程》本身并不能证明620股优待股就事实上终止了,但是在证明620股优待股已经终止这个问题上,《章程》是有贡献的。“一块砖不是一堵墙”,麦考密克的经典格言在此案中得到完美诠释。它也是最终事实这堵墙上的一块砖。
再说《借款协议》。孟文指出:“借款协议第九条和整个借款协议白纸黑字,有哪一个字提到以红利抵扣590股现金股?”据此,孟文认为借款协议只能证明商志才有交还红利的义务,不能证明一审被告拥有抵扣590股现金股的权利。本文认为,借款协议用以证明的事项,是公司有权主张商志才交还红利,由于商志才未交还红利,公司以590股现金股作了抵扣。所以,该借款协议在一审被告和最高法院判决书中,并不是直接用以证明被告有权抵扣590股现金股,而是在确立商志才应当交还红利这一前提下,间接证明公司有权抵扣590股现金股。李四欠张三100万,张三手里拥有李四1万股股份,因李四未清偿欠款,张三用李四的股份抵扣,这个问题应当属于常识吧。借款协议实际上想要证明的事项,并不是根据借款协议的文字本身就能够得出新和成公司有权抵扣股份这一结论,而是590股优待股作为清偿红利的对价,已经抵扣。后面这一事实当然是能够左右案件结果的事实,具有实质性。有没有证明性?原理同《章程》,具有证明性。所以,有关联性。
最后,1375股分红单。孟文认为:“1375股分红单就是一张分红单,能够证明商某领取了1997年1375股的红利,除此以外,没有其他证明意义。”本文对此完全不能赞同。分红单与本案有没有关联性呢?还是老套路:先看实质性,再看证明性。实质性怎样判断?当然是看这个证据要证明什么。它要证明什么呢?要证明商志才接受了1375股分红这个事实。这个事实对于决定案件结果有没有作用?当然有了。接受了1375股分红的事实,就意味着对590股现金股和620股优待股的权利都不存在了呀。所以它有实质性。再看证明性,一张有着商志才签名的1375股分红单,不仅能够证明商志才在1998年领取了1997年的分红,而且能够证明商志才知道公司在1998年只给他按照1375股分配红利。一个大学教授在自己的工资单上签名领取了10000元的工资,不仅能够证明他领取了这份工资,还能证明他知道自己的工资是10000元;甚至更远一点,他还知道这所大学在羞辱他;再远一点:他接受了这份羞辱。
四、本案中的举证责任分配
说完了关联性,该说举证责任了。最高法院判决书认定:“1998年5月,该化工厂作了97年分红清单,商志才签字领款,该清单中股份分为现金股和优待股两项,清单上其他人均有不同数额的优待股,商志才优待股一栏记载为0。此后多年,商志才也未主张过优待股,证明商志才对于取消其优待股是认可的。”“商志才称其仍然拥有上述1210股股份,但却在1998年之后长达10年时间里未主张权利,确与常理不符。”
对此,孟文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9条,商志才拥有2585股股份,被回购1375股股份,依加减乘除的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商志才还有1210股;对此事实,由于原被告双方并无争议,因此应当由被告承担证明原告对1210股股份权利消失的举证责任;原告未能举出相应证据,应当承担其主张不被认可的后果;绍兴中院未要求被告举证证明原告持股权利已经消失,反而要求原告举证证明其曾就分红问题向被告主张过权利,显然是颠倒了举证责任;浙江高院和最高法院均以商志才1998年之后长达10年时间里未主张权利推定出商志才不拥有1210股权利,这是武断强加额外的举证责任给商志才以否定其持股股权,“完全违背程序法和实体法的常识与规则”。
本文认为,孟文关于被告人应当证明商志才1210股股权已经消失的立论是正确的,但是关于被告方完全没有举证证明的说法却不正确。如前所述,1998年分红清单作为证据具有关联性。这一证据能证明什么呢?它能够证明(1)1998年5月分红时,清单上分别列了现金股和优待股两项;(2)其他人均有数额不等的优待股,商志才没有;(3)商志才在这份清单上签名,证明其知道从此时起自己已经不再领取优待股的分红。这份清单本身当然不能证明商志才已经放弃了优待股的股权,更不能证明商志才没有主张过该优待股的股权。但是,按照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商志才是否应当有所行动呢?应当。除非商志才是亿万富翁,根本不在意那点股权。从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1998年商志才刚刚博士毕业,显然不是亿万富翁;从他最近这几年为这笔股权提起诉讼的情况来看,商志才应当是很在意这笔钱的。那么,为什么在1998年之后的10年期间,商志才都没有主张过该股权,这难道不是令人疑虑的事实吗?证据就是证明的根据。商志才从1998年5月就清楚地知道他已经不再领取那620股优待股的股权了,这是一个事实;从1998年5月起的10年里,商志才也没有主张过这620股优待股的股权,这也是一个事实。这两个事实,都是从本案证据中推导出的第一步的事实结论,从这两个事实结论再推导出商志才已经放弃了620股优待股的股权,难道不是顺理成章,难道不正是符合孟文所称的经验法则吗?法院从被告方的这两个证据出发,在原告没有举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认定商志才不再拥有上述股权,怎么就不符合成文法规定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了呢?
当然,本文并不是说,从上述两个证据就一定能够百分之一百地推导出法院所认定的结论。本文只是说,声称法院对上述结论的判断完全没有任何证据,是不公正的。法院判决是有一定证据支持的,被告方是履行了一定的举证责任的。在被告方履行了一定举证责任的情况下,原告方没有进一步举证反驳对方的主张,是要承担其主张不被认可的风险的。本案最高法院在原告方未举出任何证据证明商志才自1998年5月之后曾经主张过上述股权的情况下,认定原告方已经放弃上述股权,并无不当,也没有转嫁举证责任。
至于那590股现金股,根据孟文的交代,该案二审中被上诉人也就是一审被告答辩状指出:“双方对扣减590股现金股以抵作应缴还的108000元红利已达成事实上的合意”,一审被告提供了章程(草案)、借贷协议和1375股分红清单,来证明双方就590股已被作为抵偿108000元应缴红利达成事实上的合意这一事实。对此,孟文指出:“一审被告必须对终止和抵扣1210股权这一权利变更和抵扣合同的订立和生效这两个事项举证,也就是说,一审被告必须直接证明终止和抵扣合同的存在。”“一审被告没有依照法律的要求举证,只是随意提交了三份风马牛不相及的书证,编制了一个让本案法官们觉得合乎情理的”故事,“居然得到了三级法院的认可。”
本文认为,的确,一审被告应当承担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举证责任。被告是否承担了这样的举证责任呢?本文认为已经承担了举证责任。那就是被孟文称为“风马牛不相及”的三份书证。本文认为这三份书证不是风马牛不相及,而是与案件存在关联性。这三份书证,章程用来证明商志才的离职将导致的法律后果(缴还红利);借款协议证明公司拥有要求商志才缴还红利的权利,从而间接证明公司有权用商志才的更夫予以抵扣;1375股分红清单证明商志才明了其对化工厂所拥有的股份从原来的1965股(扣除优待股之后的股份)已经减少到1375股,减少了590股。最后这一份证据,结合商志才10年未主张其股权这一事实,当然可以推知其知道化工厂已经扣减其590股现金股这一事实,并认可了这一事实。
五、法官有无突破自由心证的底线
自由心证,就是法官对证据证明力完全凭借自己的良心和理性自由地进行评价,并根据全案证据对案件事实自由地得出自己的结论。这里边实际上包含两个方面:第一是对证据的证明力大小自由地进行评价,也就是说,首先,面对任何一个证据,法官愿意在多大程度上相信它,由法官自由判断;其次,面对多个证据,尤其是相互矛盾的证据,法官究竟愿意相信哪一个,也由法官自行判断。第二是全案证据综合起来究竟能够对案件事实得出什么结论,也要由法官凭借理性、经验和良心自由判断。值得指出的是,这里说的“良心”,指的是认识论上的“良心”,就是良知良能,是人一生下来就具有的能力。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不过就是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扩充我们一生下来就具有的能力。所谓凭良心认定事实评价证据,就是凭借我们的认识外部世界的能力,以良心为基础,借助我们的经验和理性,对证据进行评价。
既然是自由心证,当然要强调其自由的方面。这个自由,就是指法律不对证据的证明力预先作出强硬的规定,而是由法官在具体案件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所以这个自由心证原则体现了亚里士多德的所谓“实践理性论”,也就是我们对外部世界不需要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基本原理,而是可以视具体情境随机应变。具体到证据证明力的判断上,也不需要通过立法者事先制定一部包罗万象的证明力法典,而是交给法官在具体的情境中自由地判断。之所以强调理性,也正是这个缘故。所以这里的理性,主要就是实践理性,是人类面对具体问题知道如何具体处理的一个具体表现。
它有没有边界呢?当然有,那就是这个词本身所包含的内容,那就是良心、理性和经验。经验实际上是我们人类理性的一部分。这部分内容是不能够以法典的形式加以固定的。例如当张三和李四都主张卡拉这条狗属于自己所有的时候,究竟张三的话更可靠还是李四的话更可靠,法律不会预先加以规定。当然,在中世纪,曾经有法律规定过,比如法定证据制度之下,曾经规定男人的证言优于女人的证言,僧侣的证言优于世俗人的证言,贵族的证言优于平民的证言。但是那个早就已经被废除了。如今没有那个国家的法律再做这样的规定(嗯,有一个国家最高法院规定“物证、书证一般优于证人证言”——参见该国《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那也只是说“一般”,但并没有对“一般”作任何界定,所以实际上相当于没规定)。所以,对于属于法官自由心证的事项,并不存在所谓的“成文法规定”的底线。
孟勤国教授关于“自由心证必须受成文法规则的约束”这一标题,我就是不赞成的。读了他的论文之后,我更不赞成了。因为在读他的文章之前,我还不确定他这么说究竟是什么意思。读了他的论文,才知道他是说自由心证不能取代举证责任,这是他的第一层涵义。关于这一点,本文之前已经分析过,孟文所针对的最高法院判决,并没有颠倒举证责任。其次,孟文说自由心证不能曲解证据及证明力。这么说似乎好像能成立,因为任何人都不能曲解证据及证明力。但是孟教授说,“当事人对证据及证明力常有争议,但这并不改变证据及证明力的客观属性,自由心证恰恰是为了揭示证据及证明力的客观属性。”这句话我就看不懂。自由心证就是自由心证,就是对证据的证明力自由判断,它何时还承担了揭示证据及证明力客观属性的功能?然后又说“如果证据证明力本身比较模糊,难免有法官自由裁量的空间。但在证据及证明力清晰的条件下,自由心证不能不顾证据文义和作用另作解释”。这其实仍然是对证据的证明方向提出的孟教授自己的看法,也只代表孟教授自己对证据的判断,却不能妨碍法官会对证据作出不同方向的判断。如果一方当事人及其律师对证据的判断就是自由心证的界限,那另一方当事人怎么办?
最后,孟教授认为自由心证不能违背常理。这个说法我也是赞成的。但是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比如在陪审团审判制度下,自由心证的主体是陪审员,基本上没有什么制度可以约束陪审员不违背常理。所以英美刑事案件中的陪审团裁决,偶尔会出现11:1的结果,在那些实行一致裁决的司法区,这样的裁决是不作数的,最后要解散陪审团重新审判。那11:1的结果是怎样出现的呢?就是因为有一个陪审员不按常理出牌,他不同意绝大多数人的意见,最后大家都被他弄的没办法,只好宣布解散。当然,有时候那1个人恰恰是对的,因为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丰富多彩的,好多事情不按常理发展的。所以常情常理并不总是正确的。在英美法系,为了保障陪审员完全的自由心证,证据法规定对陪审员如何形成其内心确信的过程是不允许传唤陪审员作证的。如果那一个投反对票的陪审员被传唤作证,问他为何作出与大多数人不一样的裁决,他说我昨晚做了个梦,梦见上帝告诉我,我就是唯一正确的那个人,大家会觉得怎样?觉得他不合情理。这样的证词披露了会怎样?会破坏司法的权威呀。所以英美的证据法不允许这么做。
在法官审判的语境下,法官对事实形成的内心确信反而可以受到一定的约束,那就是判决理由的说明。在法官审判的语境下,尤其在中国、德国这样的国家,法律要求判决书是要说明理由的。这不像在英美的陪审团审判,陪审团不需要对自己的裁决说明理由,当然也不需要揭示自己心证的过程。在法官审判的语境中,法官通常需要通过判决书的说明理由来揭示自己心证的过程。这个判决书的说明理由,就是不能违背常情常理的。在常情常理的范围内,法官的心证是自由的。但是什么常情常理,本身也不由法律来规范。因此法官除了受证据本身的约束以外,并不受有关证据证明力规则的约束,因为证据证明力问题其实是没有规则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判决书的写作是不受约束的。法官要在判决书中说明理由,要解释其推理过程,只不过他写在判决书上的推理过程,那是经过加工了的,那也不是一个具体法官的心证过程,那个论证是要受到逻辑规则、经验法则和常情常理的约束的,是不能有一丝一豪懈怠的。它一经公布,就要受到公众和法律人的检验。是否符合常情常理,法律人并不拥有比普通公众更多的发言权。
既然如此,本案法官判决的论证,其推理有违反常情常理之处吗?至少目前是看不出来的。理由已如前述。当然,孟教授对判决书的推理提出了质疑:“既然抵扣红利,为什么不抵扣那20万;595股现金股价值90.35万,以回购价计值13.57万,商志才居然同意以多抵少,商志才是一个不会算账的白痴?”对呀,本文也有这样的疑问。但是从证据来看,商志才确实在1998年的分红单上签字了呀,一个正常人从这个证据能够得出的结论就是商志才知道自己的股份减少了呀,而且很多钱的股份呀。他为什么签字呀?嗯,就算不情愿签了字,也应当有所行动吧?但是在最高法院裁判文书中,商志才显然十年内没有任何行动。对此,孟文也没有跟读者作更多的交代:商志才其实是有行动的,只是举出的证据没有被采纳,或者根本就没有证据,但是因为证据已经消灭——没有任何交代,让一个正常人如何判断商志才对扣减其股份的事实是不认可的,是持有异议的,而且是一直反对的呢?假设孟教授每月从武汉大学领2万元工资(假设是教授级别),突然从现在起每月只发10000元(假设是讲师待遇),孟教授是签字呢,还是不签呢,还是根领导折腾一下再签呢?还是过十年等现任领导都玩完了再去法院起诉呢?
综上所述,最高法院从商志才知道其权利已经被剥夺且十年未主张权利这些事实,推断出商志才与新和成公司达成了“事实上的合意”,从而不再享有相关股份的股权这一事实(特别强调:最高法院的逻辑并不是商志才知道其权利受到侵犯而没有及时主张权利所以丧失了诉权),完全符合人类的一般生活经验。在商志才未举出相反证据加以证明的情况下,其判决书将上述是推定认定为事实并无不妥。因此,至少从最高法院裁定书的内容来看,该裁定书对相关事实的推理并不违反自由心证的所谓“成文法规则”(再说一遍,自由心证就是自由心证,不存在所谓的成文法规则),也不违反一般的常情常理。至于法官形成此内心确信背后的真实原因是什么,外人都是无从得知的,也是本文所不关心的。
结语:教授是否可以批评法官
写到这里,终于可以结束这篇小文。但是还是忍不住对教授可否骂法官这个话题也说一下自己的看法。综观整个热点事件的进程,我再次领悟了中国人不讲逻辑的厉害。孟教授的论文是对最高法院裁判文书的批评。毫无疑问,其中夹杂了不少情绪化的成分。虽然我不赞成他文中对证据法问题的分析以及基于这些分析对最高法院裁判文书所作的批评,但是我认为他有权对所有公开的法律文书所载判决要点进行批判。这个问题本来是不需要的讨论的。需要讨论的是孟勤国教授文章的批评从规则、学理上是否能够成立。
然而从一开始,几乎就没有人关注这个问题。相反,所有人一上来就把战场转移到教授能否批评法官这个领域。这一是转移话题,二是偷换概念。真正的问题是法学教授对法院裁判的批评是否有理,以及批评的方式是否得当,而不是曾经代理过争议案件的教授是否可以批评法官的裁判。结果这个问题在很多评论者那里一开始就被偷换成“法学教授能否批评法官”这个话题。再然后,问题转换成“教授能不能骂法官”。一些大咖教授应声而起:教授怎么就不能骂法官?骂得好!教授们尤其兼职做律师的教授们被法官骂的还少吗?法官可以训斥做兼职律师的教授,教授怎么就不能回骂裁判不公的法官。真正的问题无人关注,大家都在核心战场之外展开激战。激战正酣,一位文采飞扬的大律师出来说:大家都别掐了,都是屌丝,互相有什么好掐的!另一位律师同样表示:没错,都是偏房的丫头,该干啥干啥去!表面上似乎公允,实际上仍然是在和稀泥。
本文不满足于和稀泥式的和稀泥,响应孟教授的号召专门就其论文中涉及的证据法问题与之商榷,算是回到战场的中心。本文仓促之间,也不可能面面俱到。由于对案情不熟悉,也不可能对案件的法律适用作全面的分析。因此本文的论述所及,仅限于证据法层面。对于按照民商法原理,商志才是否仍然应当享有其股权;以及本案中是否有法官枉法裁判的情形,本文既无力也无心加以关照。这一点很可能会让大家失望。
最后,本文虽然赞成孟教授对已生效裁判包括其自己曾经作为代理人参加诉讼的裁判进行分析和批判,但是不赞成使用这一类言辞激烈、情绪激动的方式来进行批判。孟教授的论文发表在《法学评论》这一核心期刊,自然是希望大家对论文中所涉及的问题一起来进行专业方面的探讨,而不是进行道德上的责骂。所以想必孟教授也不会介意我作为同行对他的观点提出了批评。当然,我的观点也同样会面临批评。借用林语堂先生的话说,人生在世,还不是有时笑笑人家;有时给人家笑笑。对于学者而言,还不是有时批批别人,有时给别人批批而已。因此,也欢迎大家对我的观点提出批评。但不要骂人啊。谁骂我我骂谁。
实习编辑/陈若曦
为无讼供稿/tougao@wusongtech.com